转载:公平的尺度:试论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的共赢发展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公平与发展: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论文集(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2月,页145—161。
【摘录】与 我们讨论最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既然华人社会的共同标签是中华性,或者说享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的发展关联点在哪?既然华人社会 (包括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会)存在各自不同的差异性,那么,中华性到底是共同的纽带还是发展的动力?或者既是共同的纽带又是发展的动力?我们 应该如何从中华性的历史形成轨迹中获取必要的经验与教训?问题之所以如此提出,是因为这里牵涉到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中华发展当下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节点选择,那便是:当外部世界发展乏力时,中国到底是从外部继续寻找发展的动力,还是从内部重新发掘发展的动力?反过来,当中国开始重新从内部历史文化传 统发掘发展的动力时,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文化历史传统背景在中国历史路径上却呈现出如此不同的发展繁荣与落后衰退的节点与轨迹?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中国现 代性探索需要以那种非常激进、非常剧烈的革命的方式颠覆自己文化传统呢?当下,当我们积极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发展的路径与动力时,中国是否需要警惕不要 再次陷入“中国中心论”的怪圈而重韬历史上由盛而衰、落后挨打的覆辙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一定需要一一明确回答,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问题的本质与主题的方向。
这 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作文,至少各涉及一组重大概念和一组重要主题。一组重大概念是:中华性与华人社会;一组重要主题是:发展与公平。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相 应地也分为两组。第一组为概念问题: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中华性?什么是华人社会?第二组为主题问题:关联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的层面,共赢发展的涵义是什么? 衡量共赢发展的公平尺度又是什么?这里,笔者不自量力地选择从各个概念的界定及其相互关联的视角入手,尝试在各个主要概念之间探讨关联性,尝试在各个主要 概念与主题之间建构关联性,以此回答问题,并请教方家。
1、 公平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世价值观,贯穿于古今中外,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衍进而日益发展。然而,公 平从来都是地方性的;所以,公平的理念与内涵通常都体现了具体地域性、历史性、族群性和文化性等背景特征。同样地,“公平”也从来都是相对的;所以,公平 的理念与理想通常都是不幸地以其反面存在(即现实中的“不公”)为具体支撑条件的。这应该成为我们讨论“公平”课题的两个最基本前提判断。鉴于本文关联“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的维度,笔者如下的讨论选择也主要围绕这一专门视角。[1]
首先请允许笔者从中文的词根词义开始。《说文解字》云:“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2]“平,语平舒也。从亏从八。八,分也”。[3]显而易见,“公”与“平”不仅是两个互为正面界定依托、密不可分的汉字,而且分别确立了一个对立面的道德价值维度。“公”的对立面道德价值维度是“厶”字,强调“背厶为公”;“平”的对立面道德价值维度是“亏”,强调“背亏为平”。细 究起来,“公平”之间,两者互为尺度与境界,倘若非要区别不可,“公”为主体、载体与客体,兼具政治、社会与道德涵义;“平”则为度量与衡量的维度,更多 地指均匀、稳定、和谐的状态和性质,但具体指涉却是群体的社会脉络与系列关系的机制架构,通常发生在某一有机的单元、系统、结构等框架内(包括地理的、社 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用于调节其内部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
以“公”为主体组合的关联词汇,最重要至少有三个:其一,“公平。其二,“公正”。其三,“公开”。三 者关系构成是:“公平”为最原始的内核,道德伦理价值贯穿始终;三个方面,彼此关联,依次推进。“公正”是最根本的概念,主要指贯彻“公平”理念的社会契 约、政治法律制度层面,强调制度体现与实践保障。“公开”主要指“公正”实施的政治社会舆论监督层面,强调舆论监督与认可。以“平”为主体组合的关联词汇,最重要也至少有三个:其一,“平均”。其二,“平等”。其三,“平衡”。“平 均”最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匀称,“各得其份”,没有多寡优劣之分。“平等”最主要是指内在的、本质的、义理的尊重和对等,没有特权与歧视之分。“平衡”,最 主要是指相互制约、相互反冲、相互维系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系统和状态秩序,没有偏私与倾斜之分。“平衡”的关联词汇是“平安”,“平和”,“平舒”,也即指 “和为贵”的儒家思想要义。换而言之,此谓我们现代常用的“稳定”与“和平”,其含义都是平稳、安定、安全、和睦的意思,与动荡、混乱、剧变、分裂、暴 动、骚乱、革命、颠覆、倒挂、战争等极端失衡失范状态形成对立面关照。概而言之,“公平”的涵义是指“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各得其份”、“各尽所 能”与“各得其所”等等。
政治道德价值判断上,“公平”强调“衡”与“德”的重要性。两者互为因果,“衡”是“德”的基础与目标。故 《史记》云:“德成衡,衡则能平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形于衡”。[4]同样地,史书记载了“公平”的具体背景与对立面涵义。试举例:“律有无害都吏,如 今言公平吏”。[5]“公选,谓以公正之道选士,无偏私也”。[6]“不以公正谓之奸也”。[7]这里,史书明确地揭示了德治架构下“公平”所揭示的个 人、国家和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与法则,尤其强调“公”的主体性、社会性、机制性、针对性和道德性。何谓“公”?具体而言,至少有如下重要维度:其一,“官所曰公”,主要指国家维度。其二,“事出于众人者曰公”,主要指社会维度。其三,“无私、无奸、无害曰公”,主要指道德维度。[8]重要的是,有关“公平”的这些观念,是一致性、同质性的趋同价值理想,但同时基于承认客观现实中差异性的基本对立面,强调不因贵贱、尊卑、高低、上下、贫富、多少、聪愚、内外的不同而不同。同样重要的是,有关“公平”的这些观念,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恩赐与给予,而是一种互惠的与必要的安排,因为公平价值内核失范的必然后果通常是破坏性的社会衰退、失衡、不稳定,甚至最后发展为毁灭性的政治反叛、革命、政权更替。故墨子云,天下有“三大害”:“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欺愚,贵之傲贱,富之侮贫,此天下之大害也。又与(若)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若)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9]
公平是德治的基石。历史地看,公平的基本尺度,长期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对统治者的德性要求与规范,即德治。德 治下,来此下层社会的约束力量,是沉默的、无形的和被忽视的,并未转化为机制性的、制度性的、常态性的有效反制。所以,“公平”规则的对立面意义严重后果 通常仅体现为德治的必要性警示。德治的必要性在于其破坏性反面后果,通常指是来自内部底层极端的反抗、暴动、起义,或者由此而导致外部势力的入侵。故荀子 云:“公生明,偏生暗”。[10]这是 中国封建官场的箴言。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引朱熹的解释:“寡,谓民少。贫,谓财乏。 均,谓各得其份。安,谓上下相安。[11]《中庸》认为,德治的为君之道是“知、仁、勇”三大“天下之达德”。何谓三大德性“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 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之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2]德治的为臣为官之道应该是“主耳忘身,国而 忘家,公而忘私”。[13]广而言之,德治的基本秩序与核心要义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而达至仁、义、礼、智、信的天下大同,或者“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礼仪秩序。纵观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历史,一个最显著的制度性相对公平安排是肇始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开创了中国社会追求公平的持续方 向,保持社会自下而上流动的开放性,长期成为维系社会稳定与流动的主要机制之一。[14]
公平,同样是法治的基石。进 入近现代之后,公平的这些基本尺度,已经不再是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自我德性约束和给予,而且也是双向的、自下而上的草根阶级的合理诉求与权力,即 上升为法治。孙中山提倡的“民族、民权、民生”为支柱的“三民主义”即是基于现代性的公平正义观、从中国古代德治到现代法治过渡的重要历史连接点和分水 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转折的历史大背景正是因价值失范、国力衰落、社会停滞而致的政权更迭和外部欺凌。现代民族国家架构之下,法治公平价值观所规定和调节的几大关系是:其一,个人与个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其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流动、经济分配、政治权力等几大关系。与 传统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本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经济的开放竞争性与资本货物人员信息的流动竞争性远远超远了原来单一民族国家的架构,保持民族竞 争力、社会创造力、科技创新力、文化活力与制度效率是关键。公平恰恰是如何保持国家、社会、文化、制度活力的内核价值导向;没有公平价值驱动的法治支撑, 任何国家和民族迟早会走向停滞、衰退、甚至覆灭的危险。法治社会里,公平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市场环境、政法环境、公共产品服务、社会流动渠道、基本人权与 公民权保障等方面机会均等、合理配置的制度性安排。法治的迫切性是反特权、反垄断、反贪污、反腐败、反歧视、反裙带关系的对立面需要。所以,在现代背景下,“公平”一词不仅具有抽象的秩序、制度和道德价值判断的维度规定,而且明确具有相应的国家、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具体依托。
概而言之,“公平”,既是统治者的德性要求,又是制度性、社会性的框架安排法则,同时来自公民社会的约束制衡,一直是衡量任何人类社会、国家、族群和文明能否发展进步的基本价值尺度和要求。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或者是德法兼治,不变的价值支撑始终是“公平”。
2、 中华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笔者选择使用“中华性”,而没有用“华人性”、“中国性”、“中华民族性”(虽然他们意思基本相同,但视角维度却不一样),大致有两方面考量:其一,与论坛小组讨论题目的主题依托“华人社会”相对应,“中华性”的涵盖性比较贴切和包容。其二,与论坛小组讨论题目的内涵背景指涉“中华文化历史传统”相对应,“中华性”概念更简练和方便,虽然两者无法分割。“中 华性”,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和一个国家、华人作为一个族群、中文作为一种语言书写、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文明传统以及中国历史作为一份共同的集体记忆等结构 性的显著共同标签特征和认同。“中华性”的概念,囊括了有关中国与中国人轴心关系所涉及的地域、国家、族群、语言、历史与文明等核心要素建构的原生性根本 特质。[15]
应该指出的是,固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华性的内核,但“中华性”却不是简单的“汉化”。中国是一个东方古老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 ,而不是西方式现代“民族国家” (nation-state)。在中华帝国与中华民族形成中,帝国形成与民族形成的两个进程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也一直是双向的、兼容的、彼此吸收的。所以,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进程,历史的方向与正确的叫法不是以族群为中心的“汉化”,而是以文明为中心的“华化”。[16] 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性引入中国,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大事件,“中华性”的认同与建构更多地伴随着外向型的政治革命意识形态与经济现代 化的维度进行,“儒学独尊的局面也相对地被打破了”,[17]中华文化传统的承继不幸地也以颠覆性的、破坏性的方式扬弃。然而,这却开始了“中华性”积极 对外吸收现代性新的重要进程。
中华性的族群(血缘)与文化涵义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最大共识的层面。中华性的历史涵义,一方面是长期黑暗落后屈辱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另一方面是反殖、反封建救国图强的民族主义。这是指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大历史的层面。主要表现为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与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两大潮流,但最终都合流统一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旗帜标签下。港、澳、台、海外华人社会的地方历史,反过来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下,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因而与大陆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性的文化涵义,最著名的是“文化中国”的概念。中华性的经济涵义,最著名的具体表达有“华人资本主义”或者“大中华经济圈”,前者主要是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而言,后者主要是相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现实与统一前景而言。无 论哪一种概念标签,都是某一专门维度为焦聚的,都是大陆之外的国际社会的“他者”对当下暨未来“中国”可能形态的想象与展望,都是去当下中国政治敏感度的 模糊性,而且作为关键的大陆内核部分始终却处于其中的被动角色,没有机会参与讨论。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概念标签,都表明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华人社会 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阶段和性质,都不是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存在发展次序先后之分、性质不尽相同的差异,但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市场对接、经济整合趋 势却是相向而行、不可逆转的。中 华性的政治层面,香港澳门地区与海外华人社会早已经有了共识,这些地方的华人社会各自的政治认同都很明确一致。比较敏感而有争议性主要指的是两岸政治关 系。两岸政治议题虽然存在争议,但“九二共识”业已证明是客观存在;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却从未改变过。
与 我们讨论最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既然华人社会的共同标签是中华性,或者说享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的发展关联点在哪?既然华人社会 (包括大陆与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社会)存在各自不同的差异性,那么,中华性到底是共同的纽带还是发展的动力?或者既是共同的纽带又是发展的动力?我们应该 如何从中华性的历史形成轨迹中获取必要的经验与教训?问题之所以如此提出,是因为这里牵涉到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中华发展当下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节点 选择,那便是:当外部世界发展乏力时,中国到底是从外部继续寻找发展的动力,还是从内部重新发掘发展的动力?反过来,当中国开始重新从内部历史文化传统发 掘发展的动力时,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文化历史传统背景在中国历史路径上却呈现出如此不同的发展繁荣与落后衰退的节点与轨迹?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性 探索需要以那种非常激进、非常剧烈的革命的方式颠覆自己文化传统呢?当下,当我们积极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发展的路径与动力时,中国是否需要警惕不要再次 陷入“中国中心论”的怪圈而重韬历史上由盛而衰、落后挨打的覆辙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一定需要一一明确回答,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问题的本质与主题的方向。换而言之,“中华性”的讨论是一个辨证统一的课题,实际上最终归结为一个关于中国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改革与开放关系的适当定位和道路选择的永恒命题。
3、 华人社会
概而言之,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性分析单元与族群同质性界定的概念,顾名思义,是以华人为多数族群的社会构成,或以华人作为共同族群标识的社会建构。与民族国家相对应,鉴于历史的原因,具体而言,华人社会有如下几个核心层面:其 一,指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他们都是以华人人口为大多数,同属一个国家、却拥有不同社会制度与历史经历的社会。其二,指新加坡。相同的是,新加坡是以华人为 多数族群的社会;不同的是,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域外国家。其三,指其他的海外华人社会。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以华人族群与文化为社会建构的标识;不同的 是,他们是少数族群,各自成为当地居留地国家的公民,并且他们的社会身份建构与现实地域集居的对应,不必吻合。换言之,他们是散居于世界各国居留地的本土社会的;在个别国家的个别城镇,也不排除华人可能或聚居、或占多数。需 要指出的是,这里华人社会与杜维明的“文化中国”的几个层面界定存在某些吻合的部分,但却有重要的不同:其一,作为“文化中国”重要载体的海外商界、传媒 和学界等并不包含我们这里华人社会概念范畴之内。换言之,华人社会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并不具有作为方法论工具的“文化中国”概念涵义。其二,中国大陆与港 澳台地区之外的海外华人社会,并不是本论坛关注的主要出发点和本文讨论的主要着眼点,尽管两者存在着重要关联。
顾名思义,从社会视角维度,华人社会的本质特征或者身份认同应该称为“华人性”。这并没有错。实际上,在英文语境里,“华人性”与“中华性”都是同一个词Chineseness,但在中文语境中却有着视角不同、维度不同的差异。以 “华人”族群和文化为焦点参照的“华人性”,主要强调个人对国家、少数族群对多数族群、边缘对中心、移民与同化过程中的多元性、差异性与复杂性的对立同 一。“中华性”与“华人性”之间存在重迭、互联、互通、互用之处,都强调文化与族群的维度。不同的是,“中华性”包含自上而下的地域、政治、族群、文明、 历史等维度,也可以视下而上各方的解释取舍不同而不同。“中华性”更具模糊性与包容性,既有政权主权的涵义,但也不必包含政治主权的强制性涵义。重要的 是,“中华性”的政治涉跨越了很多历史时期和很多历史朝代,不必是特指当下的“中国”政府。这是“中华性”与“华人性”的不同之处,也是包容性的“中华 性”与敏感性的“中国性”不同之处,尤其是对大陆之外的台湾地区暨海外华人社会而言。所以,本文特地取“中华性”而不是“中国性”,原因即在于此。 [18]
需 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核心层面的社会,都是一个以“中华性”为共同标识的认同。既涵盖族群与文化涵义、又涵盖政治主权涵义,指的是第一个核心层面的华人社 会,即通称的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华人社会。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华人社会的中华性,因而区别于其他层面的华人社会,其内涵更丰富、地理更接近、关系更密 切,虽然也存在社会与意识心态的差异性。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讨论指涉的重心是第一个核心层面的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华人社会。为了保持概念的完整性与全面性,有时会涉及到第二、第三个层面的海外华人社会的外延。华 人社会的一致性是族群、文化与历史等系列要素所规定的同宗同源认同。华人社会的差异性,则是因殖民主义、内战、冷战等系列要素所造成的不同现代社会政治发 展进程。华人社会既为上文中的“中华性”概念所规定,又是“中华性”概念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从历史的长期发展视角看,华人社会原来本是一个不可 分割的内在统一体;之所以形成今日不同差异性的上述华人社会,是历史原因和外部因素造成的分离所致。
具体而言,若置于更大视角背景下考察,两大历史与外部因素是:其一,殖民主义。各个华人社会发展历程都受殖民主义的深刻影响。澳门是始于1553年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问题,香港是始于1842年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台湾是始于1895年日本殖民主义的问题,1945年后兼有国共内战、东西方冷战的问题,海外华人社会是移民和殖民主义的问题。澳门、香港、台湾地区也因此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部分,连接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或中国东南沿海与南洋(东南亚)、或亚洲与欧洲的重要航线要到与贸易港口。其二,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与落后,造就了政府积贫积弱:一方面是西方殖民列强的炮舰打压,另一方面是大量移民被迫出外谋生。移民的目的地大部分主要是南洋与北美,移民的职业身份大部分也因此从自给自足的农业转为为市场而生产的工商业。加之二十世纪初开始的革命和大规模对外移民成为对封建主义的颠覆与反动的主要手段,因而造就了多元的中华性形成:大陆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此谓华人社会的“分”。
历 史经验早已证明,无论何种情况,华人社会之间互动与连接的大势却始终是相向而行、越走越近的。正因为如此,曾几何时,港澳台地区华人与其他华人社会都被贴 上同一个共同标签,即“海外华人”。虽然政治上被迫分离,但广大海外华人一直与祖国心心相印、同呼吸共患难。中国国内外大事件一直牵动着每一位海外侨胞的 心。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长期以来,历史上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认同于当地社会和国家,而是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相对应,而且是以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汇合统一成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大潮。一 百多年华侨华人与当代中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四个高潮:其一,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的爱国高潮。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没有华侨,便没有中国 革命。其二,抗日救亡的爱国高潮。毛泽东称赞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高度肯定华侨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其三,积极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 设的高潮。其四,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的高潮。四个经济特区的选址与设置,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始终离不开海外华人的重要贡献。
鉴 于国内内战、“文化大革命”与国际冷战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海外华人社会与大陆的联系又一次中断,而且间隔长达几十年;而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大陆越来越穷,海外华人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旺。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之后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海外华人重新与 大陆连接,再次积极充当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的大任。受新形势发展前景鼓舞,为建构海内外华人社会的一体性标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杜维明提出著名的“文化中 国”概念。[19]同时,随着中国沿海开放地区日益发展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回归的时间窗口日趋临近,“大中华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也成为当时国际学界 热烈讨论的选项。[20]当下,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随着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经济日益整合,社会发展水平差距逐步接近,交往日趋频繁,“中华性”作为一体性、共同性的标签应该更能为华人社会所接受,近年来国际学界对“中华性”的热烈讨论即为明证。此谓华人社会的“合”。
4、 共赢发展
发 展是当今世界一个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概念,专业系统性与非正式性并存,综合性与专门性兼具,有国家与社会的维度之分,内部与外部、正式与非正式之别,其 原生涵义大意指“前进”、“前途”、“成长”、“进步”、“进化”、“福祉”,以及“和谐”与“健康”等含义,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生 态、人类和人权等关联性维度,涵盖个人、社区、地方和国家层面,甚至更大范围的地区、世界与全人类的层面。一 般地,发展的程度定位是介乎于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进行状态,发展的空间定位是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发展的必要性是为了摆脱落后、贫穷、 愚昧、封闭、暴乱、专制等对立面驱动,发展的进程是从传统到现代过渡、从贫困向富裕转变、从第三世界向西方发达国家追赶。无论哪种层面与维度的涵义,公平与和平是发展的两大前提条件。前者主要是民族国家之内法治的范畴(同时涵盖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内核价值支撑;后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安全的范畴,是发展的外部环境支撑。[21]没有公平与和平,发展根本无从谈起。这应该是本论坛和本文发展概念的基本框架。
若冠以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发展相应地衍生更多复杂的涵义。从 政治经济的视角,发展等于“现代化”,涉及经济成长、民生、民主和“传统”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发展等于“西化”,涉及非西方社会的道路选择与权力 关系。这大概是发展概念最具争议、也是最根本性的关键所在。与社会的维度相对应,发展的涵义更多的是关于社会转型的公平性问题。在民族国家主权范围内,发 展的内部含义,既有系统性、一揽子的模式与道路选择,如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文化等协调综合可持续性内涵等等,又有特指与贫困落后和富强发达相关 联的专门性涵义。在民族国家主权范围之外,发展的外部含义,主要是地缘政治经济的课题,或者“战争与和平”的课题,或者“发展与合作”的课题,或者“控制 与依附”的课题,既牵涉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互惠共赢合作,又关系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分歧,甚至霸权对立冲突。
笔者相信,本次论坛华人社会的发展应该主要是指:其一,宏观战略层面的且广为接受的涵义。其二,正面、中性、去意识形态争议的涵义。具体而言,相应地应该首先是国家发展、和平发展;然后主要指华人社会层面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等等。把 “华人社会的共赢发展”单独作为一个课题来讨论,本身很有突出和彰显课题的意味,直接或间接,至少应该如下几层含义:其一,强调“华人社会”,本身即承认 华人社会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存在上述几种不同性质不同的差异性,虽然都共同拥有“中华性”的特质性认同。其二,强调“共赢发展”,表明这既是一个历史战 略大机遇与大势趋,是不可阻挡的,同时暗示问题仍存在争议、怀疑、甚至部分反对的声音;既意味着各方对“发展”方向仍有待取得共识,同时暗示达到“共赢” 的局面仍有待努力。其三,强调“华人社会的共赢发展”,意味着这是一个中华性标识下的华人社会互惠正面的发展,与国家之间政治霸权与零和游戏乃至共赢的性 质存在根本不同。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华人社会“中华性”标签认同之所以形成,除了自身族群、文化、历史等内部“自我”因素规定外,还存在一个共同的外部“它者”因素规定。换而言之,与外部之间分歧合作方式和性质根本不同的是,华人社会的差异是内部之间的差异,华人社会的发展是内部之间的合作。
有 鉴于此,大陆与港澳台地区需要思考这么一组密不可分的大问题:对华人社会而言,共赢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与最高福祉应该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个节点时机强调 “华人社会共赢发展”?反过来,对华人而言,共赢发展的最危险趋势与最大危害又是什么?哪些势力最不希望看到华人社会的共赢发展?共赢发展的条件和机遇是 有什么独特时代特征?为什么?等等。概而言之,还可以这样问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世界大潮,浩浩荡荡;“共赢发展”是关于华人社会的战略选择与根本出路的原 则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意愿问题而已。如上文一样,这些问题也可以不必一一明确回答,但如此提问可以帮助我们厘清问题的脉络和实质。
5、公平的尺度: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的共赢发展
在上述背景下,鉴于华人社会的不同发展历程,如果把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相关联讨论,那么中华性既有共同的原生性、一致性标签,又有各自不同的差异性。就整体性板块、结构性关系而论,争论的核心是:谁是中华性的合法性代表与垄断话语权的合法性解释者:到底大陆,还是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与其他海外华人社会?如 果撇开其他海外华人社会,这实际上涉及中央与地方的特殊关系问题,以及各个不同的华人社会呈现的“不同华人性”的问题。“中央与地方”特殊关系的问题,不 是中心与边缘的霸权关系,而是尊重历史与现实差异性基础上的“一国两制”的关系。各个华人社会呈现出“不同华人性”的问题,不是平行的、独立的“华人 性”,而是同根同源、拥有根本一致性的华人性基础上而衍生的差异性。特别是对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而言,差异性,指的是因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 背景下,而呈现与大陆华人社会的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
就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的具体关联而言,共赢发展的基本要义应该是:首先,与内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涵义相比,共赢发展首先应该是国家发展,此即华人社会共赢发展的首要政治性涵义。国家发展固然有民主化的内涵,但对华人社会而言,当下最重要的课题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经 济与社会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基础,国家发展是最重要的原则和共识,其外延却更广泛,牵涉外部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要素。国家发展,或曰国家统一与民 族强盛,或曰和平发展,或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曰中华文明的传承与繁荣,应该成为华人社会共赢发展的最大共识和最高原则。其次,是各个华人社会的和谐 发展,即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人社会各自的和谐发展。当下大陆正在建构法治社会,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可持续发展。鉴于港澳台地区华人社会对此已经积累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应该加强相互交流,港澳台地区某些成功的经验与有益的教训尤其值得大陆借鉴。
与几十年前相比,华人社会共赢发展的一个显著不同特征是: 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对称,前者是封闭、贫困、僵化、落后的计划经济,后者是开放、先进、生机勃勃的东亚小龙,经济优势的天平向港澳台地区严 重倾斜。如今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天平则向大陆严重倾斜,港澳台地区经济融入大陆市场,而且被大陆赶超的压力越来越大,相比而言,心理优越感不再,社会普遍 焦虑烦躁,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进而转向保守,强调自身的差异性与身份认同,并以民主化发展诉求为爆发点,与外部地缘政治经济要素交织,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这应该是华人社会共赢发展需要克服的两大重要挑战。
当下,华人社会共赢发展最突出的现实前提和战略机遇是:首先,是中国崛起;其次,是亚洲崛起。两者相互关联,彼此依托,相互促进。“一 带一路”既密切连接着中国与亚洲内部各地区,又把中国与亚洲之外的欧洲、非洲大陆紧密连接在一起。人员往来、贸易物流、高铁技术的互联、互通、互补是条 件,也是动力;实施中的“一带一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保障,也是基础;已经实施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谈判结束、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是架构,也是前景。如此,中国通过丝路贯通欧洲,与大西洋对接;通过亚太连接美洲,与大 平洋对接。中国与亚洲构成一个巨大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崛起依托于亚洲的崛起,亚洲崛起依赖于中国崛起。无 论是中国复兴,还是亚洲崛起,都将面临几大问题:其一,动荡与稳定的关系。这是国内的维度。其二,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是国际的维度。其三,传统与现代的 关系。这既是国内、也是国际的维度。其四,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这同样既是国内、也是国际的维度。所以,共赢发展,一方面浩荡大势,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又有 大我与小我、大前提与小前提之分,族群、文化、历史与意识形态之别。
三个相互关联的客观现实要求同样非常重要: 其一,发展永远是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第一要义”,是不可改变、也不可阻挡的战略抉择和历史大势。其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华人社会积极融合大陆的 发展第一要义,进而反过来整个推动大陆发展的重要推手,并最终汇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和大复兴,是谓“共赢发展”。其三,发展的外部要素,即世界局势、 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是中国大发展的外部环境与重要历史机遇,但前景却永远不会平坦,不会乐观。前 两个因素是内部问题,应该成为华人社会的共识,无论是对大陆,还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或者海外华人社会而言,都是如此。最后的外部因素有些复杂而吊 诡,原因很简单,即西式民主化的诱惑与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扰。内外要素,往往会相互影响,相互转化,有时甚至汇合在一起,都需要积极应对,努力经营。无论内 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华人社会所面临的中华性与共赢发展的基本前提首先是国家和平发展,这是关乎经济、政治、社会等其他层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次才是发 展路径与发展层面的问题,这既需要考虑你我、内外和中西之间选择和认同的大是大非问题,同时需要考虑华人社会内部存在的历史差异性现实。“和而不同”的儒家要义,应该是一种大智慧。另一方面,诚如杜维明所言,“儒家传统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以大事小靠仁道,以小事大靠智道”。[22]复杂难解的政治很多时候需要从族群、文化和历史的脉络中寻求公平解答的智慧。
应该承认的是,就 国家与社会层面关联而言,发展与公平既是双重尺度,也是互为彼此尺度。公平作为一种尺度,通常是指衡量发展的社会与政治权力关系维度而言;发展作为一种绝 对尺度,通常是关于福祉、前途和命运的课题,尤其是指对立面意义关联更具针对性,如亟待改变的贫困、饥饿、愚昧、落后、依附等等状况。公平,是普世价值, 有社会、国家、道德的维度,是人类价值观的基本愿望,也需要制度性安排来体现和保障。发展,是硬道理,有经济、社会、政治的维度,特别是当下第三世界新兴 经济体的第一要义。中华性,是身份认同,有地域、族群、历史、文化的维度,是我们华人社会的共同纽带与内在动力。无论是公平,还是发展,都没有绝对性,都 是地方性的和相对性的,都具有特定国家、族群、文明与历史的具体背景条件和特征。公平需要发展为基础,发展需要公平为导向。公平,离不开中华性的价值底 蕴;发展,需要从中华性中寻求驱动力。华人社会与中华性关系,也是如此:华人社会因中华性而凝聚相连,中华性因华人社会而承继丰富。无论是公平,还是发 展,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一厢情愿的。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没有公平,发展不会持续,迟早会陷于停滞;没有发展,公平没有基础,无法真正体现。
中华性是华人社会连接的纽带,也是华人社会发展的动力。公平的尺度是华人社会的共赢发展,也是国家统一强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 何认识处理以下的关系,对中华性与华人社会共赢发展的讨论尤为重要:其一,华人社会内部,作为内在尺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作为外在尺度的国家发展的统一。 其二,作为中华性一致性认同与华人社会内部社会与意识形态差异性的统一。其三,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在传承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对外交流的统一。中华性有政 治含义,但不是政治霸权,血缘、文化与历史永远无法割舍动摇。中华性是根本性、综合性特征,但不是本质论,中华性始终是开放性的、融合性的,华人社会的多 样性与丰富性同样构成中华性的重要财富。在台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颁奖典礼上,美国华裔余英时教授的一段致辞很值得我们深思:
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完全可以和其他古文明如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等相提并论。和以往不同,在重建和阐释中国文明的演进过程时,我们开始摆脱 西方历史模式的笼罩。换句话说,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演进模式可以对中国史研究具有参证和比较的作用,但中国史的重建却不能直接纳入西方的模式之 中。我们现在大致有一个共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主要在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之下,前后经历了多次演进的阶段。但为了对于中国文明及其动态获得整 体的认识,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然而这绝对不是主张研究方法上的孤立主义,恰恰相反,在今天的汉学研究中,比较的观点比 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重视。原因并不难寻找。中国文明及其发展形态的独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比较和对照之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建立起来。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采取完全孤立的方式研究中国史,其结果势必坠入中国中心论的古老陷阱之中。[23]
[1]当 代国际学界正义思潮的介绍与讨论,相关文献非常丰富。有关部分请参阅[奥]凯尔森:《什么是正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8期,第 6-9页;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姚大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贾中海、温丽娟:《当代西方公平正义理论及其元哲学问题》,《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第17-20;司春燕:《法与正义关系的历史 考察》,《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39-142页;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67, No.2 (April 1958),pp.164-194;Patrick Neal,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or Metaphysical”? Political Theory, Vol. 18, No. 1 (February1990), pp. 24-50;Alan M. Hay, “Concepts of Equity, Fairness and Justice inGeographical Studies”, Transactions of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20, No. 4 (1995),pp.500-508.
[2]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卷二。
[3]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卷五。
[4]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
[5]《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6]《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8]陆爾奎、方毅等编:《辞源》(上),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
[9]转引自:谭保斌: “论墨子公平正义观”,《湘南学院学报》,2011年2月,第32卷第1期, 第23页。
[10]《荀子•不苟》。
[11]朱熹:《四书章书集注》,论语集注卷八季氏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9页。
[12]朱熹:《四书章书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31页。
[13]班固:《汉书•贾谊传》。
[14]刘后滨、董文静:《论制度设计中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以科举制的早期发展为中心》,载关世杰主编:《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5—347页。
[15]近 二十年来,尤其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际学界对“中华性”或“华人性”讨论,非常丰富热烈。有关此课题详细、综合讨论,请参阅Wu Xiao An, “The Discourse on Chineseness and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2014年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提交大会演讲论文,2014年6月20—21日。在此基础上笔者撰写的长篇英文论文, 已以“In Search of Chineseness:Conceptualization and Paradigms”为题收入会议论文集,正在出版中。
[16]Ping-ti Ho, “In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7, No.1(February 1998), pp.123-155.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岱年序,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18]吴小安:《概念脉络、文化关怀与比较视角:华侨华人研究的再梳理》,载李卓彬主编:《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馆纪念特刊》,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第75—81页。
[19]Tu Wei-ming,“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as the Center,” in Tu Wei-ming, The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34.
[20] Harry 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er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6, Special Issue: Greater China(December 1993), pp.660-686; 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No.136(December 1993), pp.926-948;Sung Yung-wing,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Mainland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
[21]相关讨论,请参阅:Manfred Stanley,“Social Development as aNormative Concept”, The Journal ofDeveloping Areas, Vol. 1, No.3 (April 1967), pp.301-316;Alejandro Portes,“On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Issu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No. 1 (July 1976), pp.55-85;Harold A. Wood,“Toward a Geographical Concept ofDevelopment”, Geographical Review,Vol.67,No.4(October 1977), pp.462-468;Immanuel Wallerstein,“The Development of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SociologicalTheory, Vol.2 (1984),pp.102-116;Frank W. Young, “Durkheim and Development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Vol.12,No.1 (March 1994),pp.73-82;Joseph A. Schumpeter,Markus C.Becker andThorbjørn Knudsen, “Development”,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3,No.1(March 2005),pp.108-120.
[22]杜维明:《对话文明》,载关世杰主编:《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23] http://news.ifeng.com/a/20140918/42021382_0.shtml
Share:
公平的尺度:试论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的共赢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pI7ivMLkpHKQt3RVKiu4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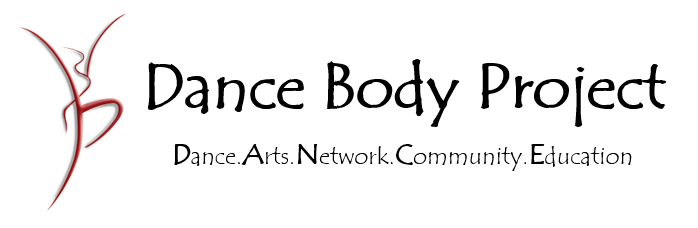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