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解讀舊馬來人的「新」困境
馬哈迪表面上成功地將馬來人推向國際舞臺,但卻將國族的共同體給分裂了,因此,一種經由以犧牲國族共同體的方式來想像馬來民族共同體,把其他友族想像為敵人,最終即是加深了國族分裂的正當性,而今,國家陷入危機之際,只好一再的暴露出其傷口,這個傷口不容外人碰觸,寧願傷口潰爛也不容他人質疑。他為敗家仔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理由,他不僅犧牲了三代馬來人,也借由犧牲了這個國家才真正突出了國族的存在,陷國族於真正危機之中:馬來西亞人的困境。
【文/曾慶豹】 December 1, 2015
一連串的政治醜聞以及經濟危機,儘管激起了國內和國際社會輿論的關注,直指首相納吉應為此負責,然而,他的位子仍然豎立不倒,前首相馬哈迪要絆倒他也無計可施。事件發展至今,問題應該不僅僅是出在納吉身上,無疑的,這已經是國家的結構性問題,這個結構性問題主要即受制於意識形態問題,說白一點,也就是長久以來一直利用並深化了的「種族主義思維」。
馬哈迪曾以一本《馬來人的困境》(1970)躍身作民族英雄,並以救世主的形象將馬來民族帶上前所未有的驕傲和光榮,從「2020宏願」到「新馬來人」,而今一切都成了泡影,馬哈迪眼見過往的努力將付諸東流,但也回天乏術,今天馬來西亞的困境也就是馬來人的困境,可謂成也他、敗也他。馬來人依然是原來的馬來人,他們已走入新的困境,這樣的困境正是原來想擺脫的,歷史的發展卻玩味地將之帶回比過往更沒自信和封閉,一個尚未出生的民族卻斷送了他的大好將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馬事件爆發以來,馬來社會不是沒有反應,但是他們的心裡是複雜的,反應是矛盾的,甚至越來痛苦越走回頭,各種保守主義的「心理反應」就表現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中,再次的塑造自己的困境以備作反抗現實困境中所落得的尷尬。
我們極其憂心的,正是這種「啟蒙辯證」的悖論,就像家裡的孩子不斷的出錯,為舒緩內心的傷痛,其做法只好不斷地把原因推給別人,或是找到別的理由做為反撃,而不願直接的面對問題並承認錯誤,從服裝到手推車,從隱性到顯性的「種族隔離」,將制造更多預想不到的衝突,很可能應驗了林吉祥的「不定時炸彈」,走回歷史的老路。
 (照片來源/Portal Rasmi Berita Malaysia)
(照片來源/Portal Rasmi Berita Malaysia)
分裂國族共同體
犧牲國家整體利益
馬哈迪並沒有想成為「國父」,而只滿足於當一名「家父」,理由是他要打造的是Bangsa Malayu而非Bangsa Malaysia,所以他並沒有把這個國家帶進現在意義的國家(Nation State),而是封建的家國。馬哈迪表面上成功地將馬來人推向國際的舞臺,但卻將國族的共同體給分裂了,因此,一種經由以犧牲國族共同體的方式來想像馬來民族共同體,把其他友族想像為敵人,最終即是加深了國族分裂的正當性,而今,國家陷入危機之際,只好一再的暴露出其傷口,這個傷口不容外人碰觸,寧願傷口潰爛也不容他人質疑。
馬哈迪通過了想像的馬來人的成功而犧牲國家的整體利益,表面上與其他民族合作,但卻是反過來去制造更為內聚力的民族認同,儘管在他任內對不同生活模式還表示寬容,但面對國際社會的打撃,卻不從整體國家的發展來考慮未來,他的一切指導性思維,仍然是「馬來人的困境」。他制造了「馬來人的困境」的焦慮並嘗試化解它,但到了納吉手上,這個「馬來人的困境」的焦慮卻被利用來躲避他無力於化解的難題,救世主的想像在無能為力的接班人手上,成了一個自殘的武器。
「馬來人的困境」的民族精神分裂:壓抑與強迫行為並用。舊馬來人的「新」困境即在於不能提問馬來人利益至上這個偉大的圖騰,任何濫權者都可以將之當作護身符,以保護自身的利益,因為他本人握有權力,只有擁用權力的才可能有能力維護它。這是一項禁忌,它甚至可以將之升高到法律的層面上予以捍衛。馬來人已習慣於一種認知,其他的民族可以有宗祖國退守,他們只有這塊土地,所以他們加深對封建統治者的認同以及宗教信仰的強化,以表現出退無可退的決心,這樣的舉動是可以不考慮到其他民族的感受的,因為他們尚未進入「國族」階段,未進入現代意義的國家來思考問題,因而,任何引起他們的危機的事務,都是馬來社會「隱性的敵人」:非馬來人、非穆斯林。
所以也就越來越難接受任何形式的「反省和檢討」,因為馬來至上的價值是不容檢討的,即使船要沉沒,也只有死守著這條原則,要死大家一起死。馬來社會不會不知道納吉所帶來的問題,他們也不是不想改變,只是他們害怕改變將失去一切。未來是不可知的,馬哈迪的輝煌也已經過去,權力不在他手上,他不能給馬來社會如同過往所承諾的,況且他的承諾也未能兌現,面對現今的困境只能越抓越緊,不能連絲毫擁有的付之一炬。當他們越感絕望,友族越發挑戰他們的領袖,他們越來害怕,一種失去自尊的絕望心理狀態,都會導致人去擁護罪犯變為「英雄」,尤其是如此巨大的風暴都絆不倒他,民間會認為,這種情況正好證明他的英勇,正當性壓倒合法性。
從民族走向宗教
擁抱宗教原教旨
公民社會發出越大的壓力,換來的是越多的反感,擔心馬來人的地位會被反納吉的壓力之下被剝奪。他們憂慮權力的重新分配帶來更多的不確定,心理上則是以偏見、不信任、恐懼,乃至發動預防性的言詞攻擊,提醒上升為「社會衝突」,因為他們根本就看不到納吉下臺以後還有誰可以支撐起這個維護馬來人的政府,所以他們只好孤注一擲將自己與納吉的命運綁在一起,並同時不斷地回到以宗教語言制造的分離和認同,來宣稱民族救贖的出路,即便沒有了民送英雄或保護,他們認為自己還有未來,這個未來即是期望於彼岸。
所以,國際和國內一樣,越不安全的時代也就越會擁抱宗教原教旨。馬來人的未來將從民族主義走向宗教主義,當英雄走下神臺,正是他們走上神臺的時候,這是舊馬來人的「新」困境,同時也是這個國家將進入顯性的「種族隔離」的社會,這是兩代人的精神狀態。這病不致於死,但要治癒真的很難,除非我們先承認真的病了,不能在甘榜找巫師做法了,也許要走到城市的大醫院須要一段很長的路,但路再長也可以走到,問題就在於是否勇於走出甘榜,走向代表著現代國家意義的「城市」,它們分別代表著不同的世界觀,所以馬哈迪把雙峰塔打造了起來,但他卻把馬來人的思維留在甘榜。
馬哈迪已無望於像李光耀那般的榮耀,有人為憑弔他的離世排隊、哭泣。他為敗家仔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理由,他不僅犧牲了三代馬來人,也借由犧牲了這個國家才真正突出了國族的存在,陷國族於真正危機之中:馬來西亞人的困境。
二十年前,本人出版的《與2020共舞—新馬來人思潮與文化霸權》(1996)一書,現在讀來,感受極為矛盾,書中所言的集體潛意識,不幸竟一一浮現了出來,令人不勝唏噓。
曾慶豹 –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邦令金人,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著作包括《上帝的愚拙與聰明的人》、《哈伯瑪斯》、《上帝、關係與言說》、《信仰的(不)可能性》、《約瑟和他的弟兄們》等。
Source:
转载:解讀舊馬來人的「新」困境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1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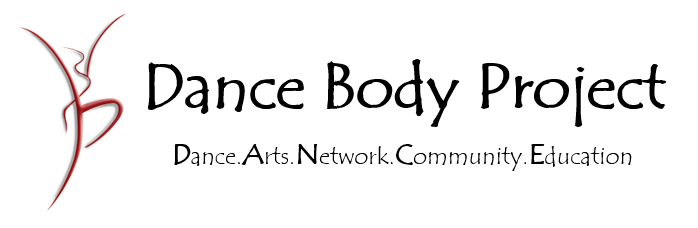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