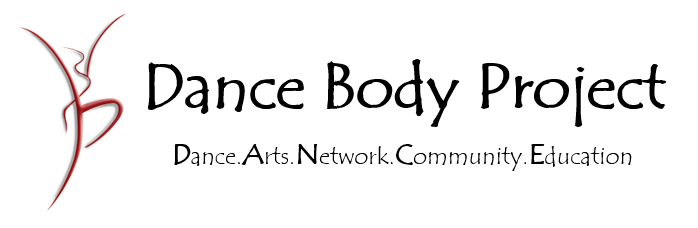转载:《火花!藝術勞動‧買定離手》:藝術勞動的呈現與實驗
繼今年推出新書《我愛Art Basel-論盡藝術與資本》後,梁寶山最近策劃的《火花!藝術勞動‧買定離手》,繼續探討藝術和勞動的議題,並進一步進行了一個資源分配的實驗。
Dance Body Project (DBP)
Founded in 2012 based on individual vision that aims to bridge the body, the dance and the community. DBP is dedicated to encouraging creative and/or explorational cross-disciplinary dance endeavours. Ultimately, DBP strives to promote education through performing arts. Focusing on four trajectories i.e. #1 performance-based research / research-based performance, #2 talks / discussion, #3 field practice and #4 documentation, DBP earnestly believes that ‘everyone can D.A.N.C.E.’!
dancebodyproject@hotmail.com
繼今年推出新書《我愛Art Basel-論盡藝術與資本》後,梁寶山最近策劃的《火花!藝術勞動‧買定離手》,繼續探討藝術和勞動的議題,並進一步進行了一個資源分配的實驗。
哲学,它思考电影的可能性是什么?如何进入电影的问题中呢?怎样介入到这种矛盾关系中呢?也就是说,哲学怎样思考电影成为大众艺术的能力?因为电影不总是大众艺术,有一些先锋电影,有一些贵族电影,也有一些难懂的电影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电影史知识。但电影始终存在成为大众艺术的可能性,而哲学则必须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哲学必须进入到这种“不是关系之关系”这个问题中。作为一种断裂,电影在人性的历史中是什么样的?电影诞生时人性与什么发生了断裂?人性在电影产生之后与没有电影时有区别吗?在电影之出现与思想之可能形式之间,内在的关联是什么?
莫扎特 4 岁开始学钢琴,6 岁在欧洲进行巡回演出,他的才能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了大量刻苦的练习,他的父亲甚至放弃了宫廷乐师的工作,全力培养他。
2014 年,日本心理学家榊原彩子招募了 24 个年龄为 2-6 岁的孩子,组织他们进行长达数月的训练,目的是教他们如何通过声音来辨别钢琴上弹奏的各种各样的和弦。完成训练之后,所有孩子都培养出了完美音高。
天才是训练的产物,无论基因遗传可能在“天才”取得的成就中发挥着什么作用,他们和我们一样,大脑和身体都有适应能力,只是比我们更多地利用了那一能力而已。
本书介绍了一种关于人类潜力的新思考方式,提醒我们自己拥有更大的力量来掌控自己的人生,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意识到。潜力好比可延伸的血管,能够通过我们一生中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创造。
由 Legacy 規劃執行的「TLCMC 流行音樂國際交流大師工作坊」,自 2015 年開辦以來,已邀集超過十位國際知名的燈光/音響師來台交流,今年主辦單位甚至將每個工作坊的三日課堂整理成逐字稿,附上中文翻譯提供免費下載,希望能透過豐富的分享,讓更多業界同好也能獲得刺激與啟發。
吹音樂特別邀請參與大師工作坊的兩位學員:燈光師秦禮盟和余明憲(橘小憲)接受採訪,聊聊自己的從業經驗,以及參與工作坊的心得感想。
中国古人并不把艺术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他们没有现代人这样明确的分科意识,而坚持认为“道通为一”,所以他们很自然地着眼于道来谈艺,甚至以谈艺来论道,艺不离道,艺即是道,它是求道、明道的特殊途径,艺以道为旨归。这样,有关道的种种思想和概念,就必然成为中国古典艺术创作的主导原则,其中有关无的种种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无是一个重要而又基本的哲学概念,中西哲学传统尽管相当不同,但都对无进行过深入的思考。由于关注点不同,中国古典美学一般并不直接讨论或论述无以及与无有关的概念。它是用感性的方式来表达和体现无。这个无乃天地之大美,无穷亦无状,非形相言语翰墨所能尽,所以简约成为中国美学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日本的藝術祭(註1)已經流行起來了,幾乎有點太流行。
除了記載在各大旅遊指南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Setouchi Triennale)和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Echigo-Tsumari Art Field,以下簡稱「大地藝術祭」)外,還有札幌國際藝術祭(Sapporo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愛知三年展(Aichi Triennale),今年新辦的有北阿爾卑斯國際藝術祭(Japan Alps Art Festival)、奧能登國際藝術祭三年展(Oku-Noto Triennale)……就連種子島,那個在九州更南的小島嶼,都搞了個「種子島宇宙藝術祭」(Space Art Tanegashima)。如果連同大小市町村舉辦的小型藝術祭計算,日本每年藝術祭數目超過365個,一日跑一個也跑不完。它們是如此受歡迎,我還記得去年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會期間,辦公室裡,餐廳裡,晚會上,道路上,經常聽到有人問答:「你去看瀨戶內沒有?」「我去過了。」或者說:「我正想去。」一時之間,幾乎形成一種空氣,甚至是一種壓力,一種誘惑,如果誰沒有到直島看那大南瓜,就好像是一大憾事,不得不擠時間,去湊個熱鬧……。
TT不和諧開講2018‧第二講我們需要戲劇構作嗎?!
主談:許仁豪(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回應:陳佾均(譯者、戲劇顧問)
主持:紀慧玲(表演藝術評論台台長)
紀錄整理:羅倩(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TT不和諧開講2018‧第二講我們需要戲劇構作嗎?!
主談:許仁豪(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回應:陳佾均(譯者、戲劇顧問)
主持:紀慧玲(表演藝術評論台台長)
紀錄整理:羅倩(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梵高》主角是大芬村畫師趙小勇,這紀錄片講述他畫了20年梵高作品後,前往荷蘭一賭梵高真跡的經歷。
上星期看了紀錄片《中國梵高》,導演余海波及余天琦到深圳大芬油畫村,拍攝那些專門繪製名畫複本的畫師。主角趙小勇畫了20年梵高畫作,生意都是家庭式經營,他跟家人和學生畫過的梵高作品多達10萬張。電影更拍下小勇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親身到梵高博物館一睹真跡的經歷。 我在戲院等入場看另一套電影時,見到《中國梵高》的預告,得悉這個故事後就覺得吸引,決定要看。
拜中華民國政府行之有年的「僑教政策」所賜,兼之以馬來西亞華人獨中統考(註一)不被大馬政府承認,這樣的「供需關係」,使得台灣的大學校園裡向來不難見到馬來西亞華裔學生的身影(但也有不少華裔學生以外籍生而非「僑生」身份來台)。
馬來西亞人主要由巫裔(馬來人)、華裔、印度裔三大民族組成,近年來已有巫裔和印裔學生來台留學,但為數相當稀少,總體而言,留台生絕大部分都是華裔,長居台灣的其他大馬人亦然。
即使身旁不乏馬來西亞人,國人前往馬來西亞旅遊者亦不在少數,但台灣人並未因此比其他國家更認識馬來西亞,對此,許多在台的大馬人都有第一手經歷,這些經歷往往還夾雜著痛苦甚至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