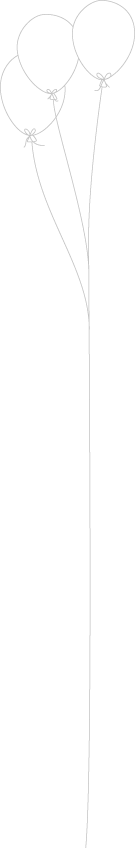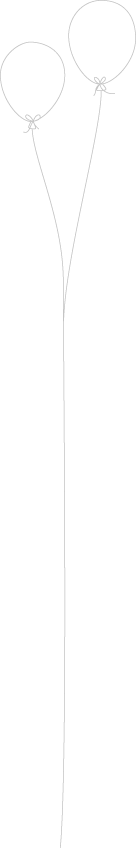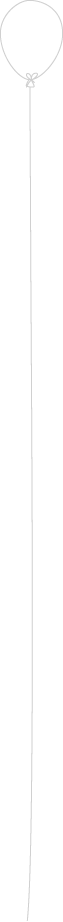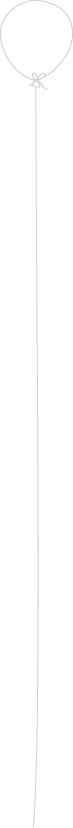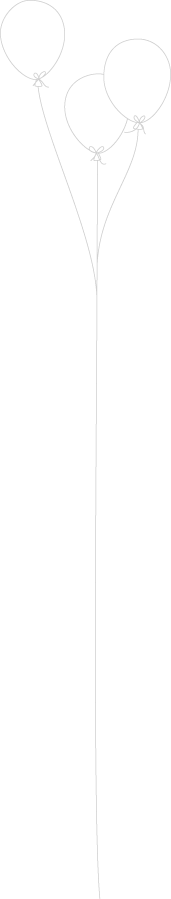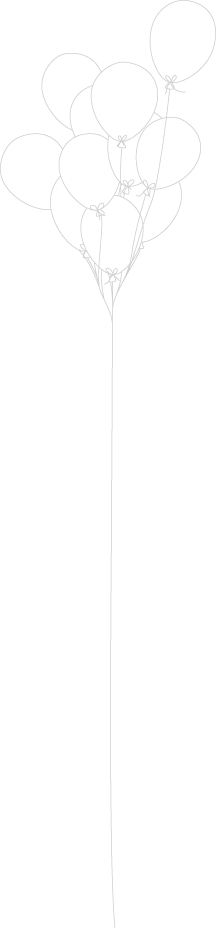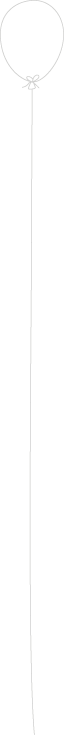從「不要臉」的劇場走出來,買了一本封面是艾未未的Ppaper,嘴裡叼著一根吸管,耳機裡放著Cicada。
然後,跌進「我/不要/臉」的反芻中。
周書毅,聽了快四年的名字,既熟悉又陌生。
從2007的【1875】到2011的【我/不要/臉】,看見了一個舞蹈表演和創作者,
逐漸在台灣藝術圈、舞蹈圈成為大家競相討論的「才子」、「新生代」。
我是越看越疑惑。
我承認,我也曾經被周先生的肢體給吸引了;但當我發現在這一張臉的背後,並不是單純大眾所看到的那張「臉」後,我開始討厭這張「臉」。
或許,連周先生都討厭。
對於周先生真正感到有興趣,是始於一篇雜誌上的採訪,主題是:「孤寂舞者周書毅的旅程」。
文章中最吸引我的一句話莫過於:「我想我對生命的感受總覺得有些缺失,但也因而得到更多美好」。
能夠有這般體會的人,總覺得那不會是一張很清晰的「臉」。
幾年下來,看著周先生的發展,逐漸邁向「do something」的階段。
不管是揚名國際,或自己一手打造「周先生和舞者們」,或立足「TED x Taipei」,周先生的表現的確讓人很期待。
但我總期待看見更inner的周先生,或者說看見下一個更inner的許芳宜。
然,這也只是我一介草民的癡心妄想。
我期待的那張「臉」,也許正是他不要的那張「臉」。
看完六十分鐘的獨舞,我無法評論出一個所以然
或許這麼多年下來,我已經很少在問自己「喜歡嗎?為什麼?不喜歡?為什麼?」。
當然,偶有例外而無法隱藏激動之情,近期就屬【斷章取義】為代表。
但看完【我/不要/臉】後,我儘速地逃離劇場,想趕快從人群中獨立出來,其實是深怕剛要開始對自己提問的情緒給打擾。
【我/不要/臉】,給我的不是什麼感受,而是一個問號?
一個周先生的?周先生對於舞蹈的?對於自己的?
我對於周先生的?我對於舞蹈的?我對於自己的?
節目單裡,排練助理林祐如寫道:「看著你這樣尋找,那個失去線性的規範,你說:又卡住了……怎麼繼續?怎麼誠實?靜默的當下如此純粹。可以的,不管有多難。」
沒錯,說出了這檔演出真正的意義。
面對「臉」,怎麼繼續?怎麼誠實?
面對自己,怎麼樣拋棄、撿拾、再拋棄、再撿拾,這是一個需要勇氣的過程。
從【我/不要/臉】,我持續地對自己展開面對這張「臉」的提問。
也許未來,再也沒有什麼機會能夠這樣了,但至少現在,我還想這麼做。
尤其,在現在我所處的這個階段上。
不管是面對畢業製作,或者是面對舞蹈、朋友、感情、家人,我不想要放棄地不斷拋棄大家所看到我的「臉」。
這真的是個痛苦的過程,真的。
。面對畢業製作。
殺青是一個階段的告別,但在感到欣慰的同時,下一秒在剪接再創作的過程中馬上就會碰壁。
它不是一個健康的小孩。
如果將它比喻成一個生命,它也許是畸形兒,那我該怎麼辦?
當大家滿心歡喜期待新生命的到來,但任誰也無法料想它的結果不是嗎?
推想結果,總不及享受累積的過程。
是,就算它是畸形兒,性別也不是當初的掃描結果,可是終究是個生命吧。
解決方法就是,鍛鍊自己,改變另一種態度,去迎向它。
我慶幸,我尚有這種想法,而我也希望,你能夠。
在這個過程中,我所犯下的錯誤和過失,都將成為一種經驗值。
討論過錯,是必要但沒有意義,誠實面對而接受,才能繼續走下去。
這條路,我還沒走完,但我已經學會了很多。
。面對舞蹈。
對於即將離開的事實,我總不希望抱有太多的遺憾或可能。
我不想留有什麼眷戀,因為那只會讓人裹足不前,而這對於未來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我知道,我不會離開它,也還好上天還算眷顧歹命人,我還有健全的身體。
如果可以,我很希望能夠做個儀式性的結束,留下一些什麼。
留下一個可以代表這四年的作品。
但也許,十年後才會完成?
年輕的時候,我們用身體跳舞;年老的時候,我們用靈魂繼續。
不變。
。面對朋友/感情/家人。
珍惜當下,
記憶過去,
感謝未來。
如果沒有這三者,這張臉,一定不完整。
【我/不要/臉】,我想要一張,不是臉的「臉」。
文字 : 杨广胜
11 April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