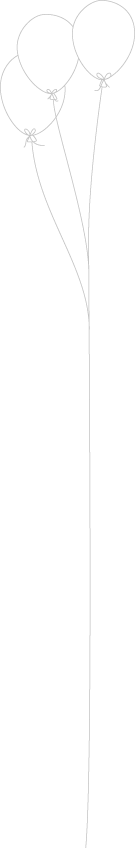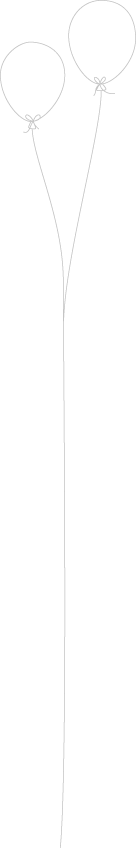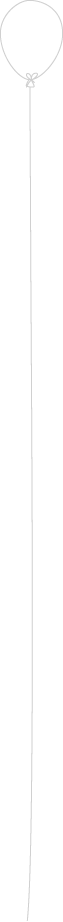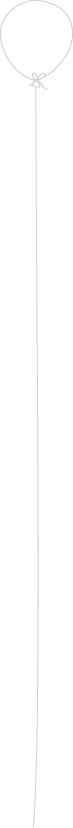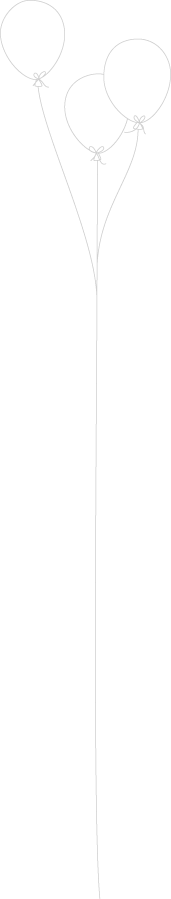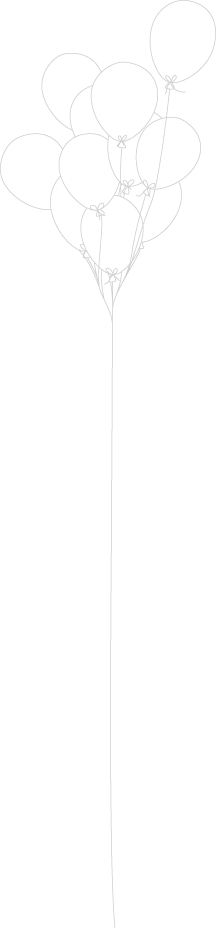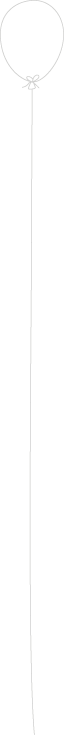如果这里的文字 (只) 是一篇演出观后感,那就对我没太多意义了。
作为一个曾游走古典、民族及现代舞的东方身体,一个对身心汇通有特殊念想、热衷咀嚼舞蹈意义、也对 ‘everyone can dance’ 笃定的探索者,一个与疫情同步迈入 (人生/事业/世界观) 转折期的新中年,在参加完被创作者Lee Su-Feh形容为演算法 (algorithm) 的“Touch Me Hold Me Let Me Go” 工作坊、也在看完它同名的讲述表演 (lecture performance) 后,我想对这一场演出中所带给我对‘身体’‘舞蹈’‘表演’等议题产生的涟漪来做一些自我梳理。所以,这是一篇日志。
TMHMLMG algorithm 在文字意义上代表着对一组问题进行运算或解决的过程,然而问题指的是什么,是她始终没有明确的事。正因如此,我在这近两个月/五年的思索后领悟到了‘舞蹈何以为舞蹈’以及 ‘in dance, mind is mind body is body’ 、‘舞蹈终该以自己的意识和感觉为主导’的确信。人为什么要跳舞,有的人寻思一生。传阅千年的《诗经》 (毛诗序) 里提到 —— 因为‘情动于中’,即情感被触动,这是多自然与存粹的身心表述。然而我们更常听到身边人给的理由往往是‘因为喜欢/好看/想上台/被安排’等。当身体经过了舞台化、剧场化、荣誉化、精美化的包装后,心里和感觉 (sensation) 会发生怎么样的改变?我们似乎没有关注过。文化舞蹈 (cultural dance) 作为一种反映集体文化记忆的形式,当前的时代审美与文化政治性又是如何塑造舞蹈身体的标符系统?我们几乎没有探讨过。相比之下较‘自由’的现代舞表演,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不刻意修饰线条、能接受舞者根据自身当下的状态调整或实验动作、还可以不依赖观众的审美偏好或满意度来评价舞者的身体表现,甚至反思票价的定位呢?我已分不清是我们的表演制度做不到 (这么开放) 还是自己的身体做不到 (这么信任自由) 了。我成了当代舞作 “Anggota”I 和 II辑 (Lee, 2021, 2023) 中所隐喻的‘不敢放开的身体’。也所以 Su-Feh 说国土上的舞者都被‘教坏’身体了,我在她这么评论以前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懦弱。
‘Touch’ 或触碰,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它的力度、接触方式、位置和时间点,可以给彼此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和印象。我记得在工作坊里她让我们允许自己按需求和喜好 (what I want/like) 去触碰有需要被关注的身体部位、倾听身体,即便是这么简单的任务而有几十年身体经验的我却纠葛了许久。因为身体的原生诉求早在舞蹈训练或适应舞作的过程中被抑制或消磨,以致自己不晓得该怎么建立‘聆听’以及信任聆听者。我按着身体的每一个伤位,默默地沮丧。作为舞者,身体 (肌肉) 最喜欢的方式莫过于可以随时 ‘动起来’,然而为了 ‘behave、有教养’ 的规范,我们不被放任让身体去随时随地地‘随心所欲’。Su-Feh 在演出里开玩笑说‘连小孩都比我们更懂得 open’!开放什么呢?她说开放让自己去 invite (身体的) pleasure、向好奇心开放、也向欲望开放。甚至是当身体遇上障碍 (如疼痛、恐惧或者欲望) 时,我们也可以作出开放式的选择例如软化 (soften) 这些障碍、直面它但也可以不接受或批判这些障碍。 ‘Touch with no agenda’, 她不断提醒我们说。当我允许自己 open to touch 那些总是蠢蠢欲动的肌肉,有一刻我终究触及了一股温热的脉动,那一天早上我度过了舞者身体经验里最自在最自由、身心合一随心所遇的一次‘舞动’,因为我的内在力量被聆听。
要对人说出 ‘hold me’ ,其实对一个东方人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还不带上 ‘please’ 的词缀呢😂)。Su-Feh 说,我们可以邀请身边的人给我们一些实际上的接触(当然对方也有权力不回应),如果身边没人我们还可邀请大地 (planet)、或者想象中的一位 ‘beloved’ 来给自己的身体各处提供一个无形的支撑。这种依循自己 (身体或意念) 的需求然后请别人提供协助的行为是很有力度的,无论是应对在现实生活的场景或是在内心自我对话时。虽然如此,我倒以为这个指令若放大来看也可以是一组社会实验,存在着对主导和顺从、礼仪和道德观上的心理博弈,体现在怎么发出和回应信息、呼应的力道、方式、时长等。甚至怎么样婉拒说‘不’,也能让我瞥见自己与他者的思维和文化差异。是否在解放我们的身体意识之前,我们更需要练习的是怎么松动从小所学的文化观?是否我们在向别人提出要求以前,也得先了解自己的个人需求是什么?个人需求怎么顺应或凌驾别人或群体的需求,我们是否有过练习?有的人提出需求成了习惯,有的人说‘不’成了习惯。舞蹈课上我们是否曾能/有过一次向老师或编导提出过‘不’?我在 ‘hold me’ 练习里经常浮现的潜意识问题是 ‘who really can’,我不得不经常躺在地上叩问大地 ‘hold me’ 乎。 (拭泪😂)
舞蹈-身体-我,是这段关系里三个‘相关但不同’的成分,也是我认为舞者都需要分别去思考和照顾的课题。我们总预设‘身体 就是 我’和‘舞蹈 就是 身体’。在舞蹈被当作是‘纯肢体运行(@精致的表演或比赛)’的主流观念里,‘我’ 的个人意识或需求(或身体需求)、‘我’是谁、我的身体是谁的、我的原生身体是/可以成为什么等问题很多时候并未在舞蹈编创的过程中成为话题。在表演理论里我们常被推向寻找一个 ‘not me’ 的舞台身份/角色/状态、极力去揣摩某种舞动风格,或是为追求 ‘versatile dancer’ 的桂冠。我们鲜少没有被赋予角色或标识、仅以纯然地存在的本我意识去舞动。这个分裂意识在我进行TMHMLMG 程式里的 ‘let me go’ 时遭到了最强烈的冲撞:我竟在下意识里反问自己该‘let-谁-go’… who is the ‘me’? 是在请别人放开我还是我该放开对别人的无条件开放?是该让紧绷的肌肉放松还是放下那对身体苛刻的想法?是该放开想继续成为舞者的痴念还是放开对舞者刻板身体形象的追求?… ‘Let me go’ 犹如一块大石,重击了我(或者说终于说服了我总不敢面对的)对过去的舞蹈概念的执念,也让我在碎片里重新找到定位并对这段关系进行了新的排列:我>身体>舞蹈。是的,没有 我 就没有舞蹈;我们都得适可而止地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他人追求舞蹈的工具,跳舞时总不能不带上‘我’(和带有身体的意识)吧!我也总认为,若把 ‘let me go’ 用在生活场景中也是一个极具力量的话术、提醒,让别人停止禁锢我们,也让我们停止纠缠和留恋在那些剪不断的思想/假想/遐想/杂念漩涡中——如 Su-Feh 打趣说的 ‘mind orgasm’ 里(😂🙈)。
TMHMLMG无疑是 Su-Feh 带给我们当代舞蹈工作者一个最好的思考演算题。不仅因为它能让人观察或练习寻找自己和身体的主权意识,也因为它的开放性让更多的个体在这个共存的社会/关系里能有效、有力量地表达‘我’自己。‘我对会陷入个人的超现实的游离,或者趋娱乐观赏性的表达/探索没兴趣’有一天她说道。‘如何能在彼此行动或发声的行为里,找到既不互相依赖 (co-depending) 但又相互依存 (inter-depending) 的集体关系’是她给我们投下的一个问题和实验目的,并且提醒我们在遇上障碍时要意识到‘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应该首先被关注到’。在她的话术里我找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伦理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看着它转移到另一层次对‘我/个人的需求’‘我/个人的感觉’‘我/个人的责任’等运用上。这个转移与我的工作状态和年龄心态来说是应时的,同时也呼应了我多年来对舞蹈教育的反思——舞蹈创作/创作者是否应具备‘社会责任’的思考。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在不少暗中受伤的舞者身体、始终成不了气候的舞蹈风气、圈内日益增加的误解/矛盾/匮乏/生分等关系里看到端倪。或许面对舞蹈我们就应该经常‘练习’ (practice) 更甚于‘表演’吧。 练习专注呼吸、练习纯粹呼吸、练习寻找发声的方式、练习在合适的位置发声、练习让身体(肌肉)力量成为发声的原动力、练习听见自己的声音、练习聆听自己的需要/渴望、练习回应自己、练习不让情绪主导感觉、练习睁开眼睛去捕捉当下、练习与别人共处一起但不干预彼此、练习在行动时不带面具、练习非必要时不做预判、练习 touch-with-no-agenda、练习be-there-simply-be、练习接受舞蹈是舞蹈/身体是身体/跳舞是跳舞/表演是表演。。。即使她也从没说过 TMHMLMG 是一个仅限于舞蹈语境的演算法,但这 body-oriented 的对话练习何尝不是一个能(以个人意识来)引领身体去促进自己作出更有行动力度的、格局更为广大的舞动意识练习法?至少,它更具智慧且人性化的打开方式是建构在舞蹈概念和身体经验上的。在舞蹈和不是舞蹈之间的,差别就是那彼此的肢体在触碰连接时的感受 – 究竟那暖呼呼的温度是来自于谁的表皮?我想一点都不重要。
TMHMLMG 以讲述表演的形式点缀着 GMBB 的黑箱,再加上 Kent Lim 能牵人魂也能纠人心的音乐设计,还有 Sam 新颖又贴体的灯光及投影,为Five Arts Centre 的跨领域实验性精神又添了一道绚丽的火花。Su-Feh 以文字作为她身体和观众之间互通的媒介,也以文字捕捉和铺垫自己的身体进入她非文字思维的状态。‘跳舞不必思考/舞蹈不需要文字’的迷思在上半场彻底被碾压。有人能说她不是在跳舞吗?即使也从未有人说她是在跳舞。更准确地说,这些文字和理解成了她后来的肢体展现的绝佳前序,让我们在用眼睛观赏她肢体游动在这空间之余,也能以自身的领悟为她带来的这些我们相对陌生的话题、道具、形式和她的身体,作了很好的连接。 ‘Lecture’ 和 ‘performance’ 状态的 ‘shift’ 是微妙的,仿佛我们观赏的也是她个人的理性和感性的移动,发生在她不说话的时候、在她的肢体动作微颤的时候、在她于人群中丝滑流动却还能保持眼神交会的时刻、在她把节奏和感受全然交给音乐和投影的时候。。。她链接的显然是她心里那一套更能兼容和共生的矩阵,用以演算她与她身体的过去、身体的现在和她意识上未见的 unknown ——‘所以这还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我也不知道它最终是什么’,她娓娓道出 TMHMLMG 对她而言究竟是什么。她的身体没有一刻是远离她意念的,也没有一个动作是曾经演练过的,许多细小的、瞬间的、在场的当下的‘moment’,与我们的体会产生了共振。在很多时刻我能感觉自己的身体和脑袋接收了比沉浸式体验 (immersive experience) 还要深刻的信息,仿佛‘表演’概念的边界被进一步掰开,从 ‘do-show’ ‘for gaze’ 的关系进化到与她一起 ‘practice’ 着TMHMLMG 程式独有的阈限性 (liminality)。尤其当她在尾声陷入‘let me go or don’t let me go’ 的自问/对观众抛问时,旁观者之一的 Marion D’Cruz 起兴舞向她并拥抱她的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了某种自身的升华 (or transformation),过渡到了自己和身体想要的永恒合一状态。能形容此刻的观后感唯有一句话 – I think I can die now,我得借用我教授的一句名言来这么说。(😂)
大语言模型 (LLM) 总结说,TMHMLMG 是一套可以重复练习的身体智慧、是一种结构开放的行动哲学,也是一组练习框架或邀约 (invitation) ,用来探索人与人、人与非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与社交实践。舞动所需的感知,与社交中建立具身化(embodiment)的能力同样重要,毕竟身体不 (仅) 是用来搬运脑袋的工具。如今的我深切感受到了(舞蹈)艺术观在自己身上的转变、自愈、超越等力量,有如植物处在阳光、雨水和大地之间那样,自然。我也得以在体验、琢磨过 TMHMLMG 后,解决了属于我个体的问题 —— 我为何/怎么存在舞蹈中;怎么在后疫情、后浪席卷和各种形式趋向固化的环境里找到一个可以让‘我’与身体持续自在游刃的对策。题解。
<Touch Me Hold Me Let Me Go> 09.03.2025 (Sun) 3pm @ FAC
Keywords :-
> “Anggota” @Lee Ren Xin — [Yang Berat Dengan Ringan]
> I-Can-Die-Now @Datin Marion D’Cruz — [We Shall Sing And Dance]
> TMHMLMG info — https://forms.gle/7tsGo96ZV3JRr8Nr8
> Five Arts Centre — https://www.fiveartscentre.org/
>lecture-performance :
A lecture performance is a live presentation that combines aspects of teaching and performance art. It’s a hybrid genre that draws on many sources, including storytell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Google AI)
>performance :
An act or process of staging or presenting a play, concert, or other form of entertainment. (Wikipedia)
>performing ‘not me’ :
Refers to the concept of performing a persona or identity that is distinct from one’s perceived “true self”. (Google AI)
>immersive experience :
A theatrical production where the audience is actively engaged and feels fully immersed in the story world, often by moving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space, interacting with actors, and experiencing the narrative through multiple senses, blurring the lines between spectator and participant, creating a more personal and impactful experienc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theatre viewing. (Google AI)
>liminality :
In anthropology, liminality (from Latin limen ‘a threshold’) is the quality of ambiguity or disorientation that occurs in the middle stage of a rite of passage, when participants no longer hold their pre-ritual status but have not yet begun the transition to the status they will hold when the rite is complete. (Wikipedia)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The first concern is affairs of state, enjoying the pleasure comes later. Quotation from essay On Yueyang Tower by Song writer Fan Zhongyan. (ChinesePod)
~ click next page for translation ~